劉忠軍:與3D打印相遇的“偶然”與“必然”

劉忠軍教授與3D打印模型
最近幾年,不論是繁忙的臨床工作,還是參加各種學術會議,甚至在履行人大代表職責時,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的骨科主任劉忠軍談論最多的話題都是3D打印技術。
一名骨科外科醫生,一項相當酷炫的新技術,兩者看似毫不相干,卻在劉忠軍的世界里,結合得完美無缺。
從世界首例3D打印的人工定制樞椎,到世界首例3D打印人工椎體,劉忠軍帶領團隊在骨科領域,尤其是脊柱外科,攻克了一個又一個世界難題,取得了令人艷羨的成績,更是引來國際同行的圍觀點贊。
而這些成績,在劉忠軍看來,他只是踐行了一名醫生的職責——治病救人。
善于提問
如果說從大學畢業進入北醫三院工作,從一名小醫生到全面執掌骨科大局,劉忠軍憑借的是一股對職業不懈的追求與滿腔的熱情。那么,當這種熱情逐漸轉變成責任與擔當的時候,探索臨床科學研究,解決病人的病痛便成為他詮釋一名臨床醫生的最好途徑。
從國內第一個引進頸椎前路帶鎖鋼板內固定技術,到全國率先開展胸腰椎前路內固定技術;從鉆研頸椎疾病微創手術治療,到推廣脊柱腫瘤的根治性治療;從獲得部委的重點項目基金,到擔任國內外骨科領域學術期刊的要職……劉忠軍憑借執著的創新能力與踏實的奉獻精神,取得了非凡的成就。
但是,他并沒有滿足這一切。
“臨床上,幾乎每個病例都有自身的獨特性,都需要我們因人施治。而也正是這種病人與疾病的差異性,才推動我們去思考更多的臨床問題。”劉忠軍認為,優秀的醫生只有具備提出問題的能力,才能更好地解決問題。
而劉忠軍正是善于提出并思考一個個臨床上的“為什么”,才使得3D打印技術與骨科有了“美麗的邂逅”。
過去,骨科通常使用空心圓柱體的鈦網作為植入物,解決骨骼支撐的問題,但是鈦網穩定性欠佳,可能會出現塌陷的現象。對此,劉忠軍帶領團隊不斷與工程技術人員交流溝通,尋求新的解決方案,但卻始終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。
恰逢此時,3D打印技術進入了劉忠軍的視野。
“3D打印技術可以做成任何形狀、任何結構的金屬物品,如果能利用這種技術,我們做成臨床上需要的形態,不就很好地解決了難題了嗎?”基于幾十年的骨科臨床經驗,他敏銳地發現了兩者的關聯性,經過跨學科、跨領域合作,歷經多年的研制及臨床觀察,他帶領團隊研制的3D打印人工髖關節產品、3D打印人工椎體產品相繼獲得CFDA注冊批準。
而經CFDA注冊批準的3D打印人體植入物,目前我國僅此兩項。即便放眼全球,這項技術也屬于領先地位。
迎難而上
鮮花與掌聲的背后夾雜著汗水,創新與探索的過程中質疑聲也在所難免。作為一項新的工藝,3D打印技術應用到醫學領域更是如此。
“熟悉骨科的醫生可能并不了解3D打印技術,而掌握3D打印技術的人也可能并不知道它能應用到醫學領域,畢竟3D打印技術最開始并不是為醫學研制出來的。”劉忠軍認為,正是多學科的交叉融合,才有兩者的“聯姻”。
但這種新的設想啟動實施的時候,質疑往往大于信任。
“新技術、新工藝、新植入物,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安全性的問題。”劉忠軍說,雖然3D打印的植入物使用的材料與過去傳統工藝選擇的材料一致,都是鈦合金,但依然會有人提出質疑:不同工藝生產的植入物強度是否發生了變化,會不會在人體內產生新的反應、造成新的危害等。
而這,劉忠軍認為還不是最難的。
“最難的是專家提出質疑背后,沒有給出太多積極建議,甚至都提供不出基本的標準可以參考。”劉忠軍也非常理解,一項新的技術產生必然要經歷這樣的過程。但他比較著急的是,歐美等國家在這方面的政策相對寬松,而我國則需要經歷漫長的審批過程。這就會導致“國內先有想法,拿不到產品,國外后有想法,卻早已經上臨床”的局面。
于是,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劉忠軍一再呼吁,要解決科技創新在政策、法律方面的瓶頸問題。“在保證安全、科學管理的前提下,將醫療科技創新產品盡早推向臨床,惠及患者”。
欣慰的是,政府的相關部門已經著手解決這些問題,也制定出相關的法律法規。但劉忠軍希望“步伐再快點”,“3D打印技術應用到醫療領域,全世界幾乎在同一起跑線上,現在就是誰走得快,誰就在前面,而誰走得慢,自然就落在后面,我們不能痛失這個機遇”。
惠及患者
不可否認,3D打印在技術上優勢明顯的確是劉忠軍為之動容的原因之一,但更牽動他內心的是科技能夠給老百姓帶來便利的同時,還能推動醫療器械國產化局面。
以骨科為例,內植物大約占據病人住院花費的2/3,“如果將3D打印全方面應用到骨科,并且實現產品國產化,不僅能夠大大降低醫療費用,還可以加速國產產品的更新換代。”劉忠軍說,相比傳統工藝產品,3D打印產品可以省去很多工業流程,只要把相關數據輸入到程序中,就能實現一步成型,節省了大量的人力成本,或許還可能實現產品零庫存的目標。
但劉忠軍卻不急于進行新技術推廣。
“剛開始,新技術還是應該交給一些資質相對比較高、有科研能力的醫療機構進行研制與應用,并且要與已經具備了生產傳統醫療器械資質的企業合作,共同研發產品。”劉忠軍認為,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保證病人的安全與利益,“如果隨便一個醫生、隨便一個工廠都去做,這樣就可能存在風險。”
針對社會上有傳言“以后能3D打印一個肝臟、一個心臟”等說法,劉忠軍覺得過于樂觀,“這或許得幾十年之后才能實現”。
比如一個肝臟,里面除了有肝細胞,還有其他細胞、膽管、神經支配系統、淋巴系統等,怎么去構建各種各樣的結構,并且讓細胞保持活力,這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。
心系國家
先進的技術、超前的理念,再加之患者的期盼,更讓劉忠軍決心把3D打印這件事堅持下去。
“作為醫學科學工作者,我們的最大責任就是用科學解決臨床問題,立足于患者的需求,為患者提供最佳的診斷和治療。”劉忠軍說,立足于整個國家的醫療需求,既要有高精尖的基礎研究,也要有短時間就形成產品的臨床實用技術,可以服務臨床、普惠患者。
但很長一段時間,我國在科研基金項目申請上,卻沒有很好地照顧到臨床。可喜的是,今年科技部的很多科研項目已經開始向臨床上傾斜。劉忠軍也榮幸地拿到一個增材制造(即3D打印)與個體定制化醫療內植物研究開發的重大專項。項目甚至明確要求“由臨床醫療單位的專家牽頭”。
“政策的利好,我們醫學科學工作者更應該牢記自己的職責,清楚自己所處的地位,把自己所做的事情與國家需求聯系到一起。”劉忠軍一直牢記科室的科訓“厚德仁術,求是創新”。
此外,作為交叉學科的受益人,劉忠軍還特別對醫學生的教育提出自己的想法:過去我們注重醫學知識的傳授與學習,但從當前發展形勢來看,確實應該多學習一些看似與醫學無關的課程,或許對未來職業發展更有意義。
“機會總是偏愛有準備的頭腦。當機會來臨的時候,你根本都無法識別這是個機會,那只能與機會擦肩而過。”看似劉忠軍與3D打印技術的相遇是一種“偶然”,其實是他善于思考臨床問題的“必然”。
(責任編輯:admin)


 王華明:潛心增材科研,也
王華明:潛心增材科研,也 金屬3D打印專家楊永強:為
金屬3D打印專家楊永強:為 Materialise副總裁:3D打
Materialise副總裁:3D打 LPW首席執行官Phil Carrol
LPW首席執行官Phil Carrol 【大國之材】許小曙:開源
【大國之材】許小曙:開源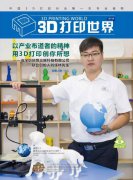 《3D打印世界》專訪創想三
《3D打印世界》專訪創想三 3D打印巨頭EOS首
3D打印巨頭EOS首 3DSystems鄧瀚誠
3DSystems鄧瀚誠 未來汽車開發者計
未來汽車開發者計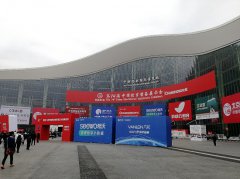 弘瑞掌舵人:3D打
弘瑞掌舵人:3D打 對制造發生深遠影
對制造發生深遠影

